����ҹ��ٿ���с����¹���ˮ���a��?z��)o���h(yu��n)̎��һƬ�峺�ĺ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棬˯��һ�߶��M���ĵׅsӿ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“�M���ǹ⣬�M���¹⣬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ʲô�@ô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o��ҹ�ʒ�t�ć@Ϣ�@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g�����M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ӂ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S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ġ�ʒ�tС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ġ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Б�ʒ�t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ʒ�t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˼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ˡ�

����ʒ�t�����u(y��)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30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֘㌍(sh��)��Ȼ��څ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࣬�ں��̎��¶���¼ţ��P�|�����w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t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ݱ����s�֎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Ԋ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ֻ�ǟo�ķ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ʒ�t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P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δ���꣬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ǝM�M��(d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ĺ��棺�@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ӵ�Ů��?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Ե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

�Ӱ���S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 ʒ�t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Ψ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µ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n��Ę���o�o�]�����촽�����ݵĄ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|(zh��)Ц��ʒ�t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䵭��İ���ġ����룬Ҫ�����˽�һ��(g��)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m�ӂ����У�ʒ�t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۵ĺ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҂�չʾ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挍(sh��)�ĺ��m�ӳǣ����Ԕ�ʽ�Ŀ��ǡ���ͯ��ҕ�X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ں��m���ذ��Ӱ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ĹP�|����һ�ќ���ĵ���һ�Pһ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и��X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ҵIJ��m���^��s�@�X����Ě��̡�
�����M�ܡ����m�ӂ�����ȫƪ��ɫ���n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ʒ�t�P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ɵ��茑�s��ȫ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ɫ�ʡ����Ќ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_�ˣ�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B�w�ˣ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x�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fԒ�Ƶġ�һ�ж����ˣ�Ҫ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ʲô;Ҫ��ô�ӣ�����ô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ġ�”���@Ƭ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游�IJˈ@������@�ʒ�t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Ěg���r(sh��)�⣺����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IJˈ@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t����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P�ء��Ի����βݡ����ˣ��游�Đ��c���B�~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ʒ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ꡣȻ�����@�ݶ̕��Đ��c���Ʌ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ɞ����@һ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Ư���ó̵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

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У�ʒ�t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^�ߡ���Į���V�f��(zh��n)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£��|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Iʒ���Ĵ��f����ͨ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݆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ݽ棬æ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Ԓ���ݵ��N�С�“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Ϳ����ֳ���y�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أ��N���Zʳ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ڄڄڵ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Ȼ�ı����̓�ֻ�_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У�ʒ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e�˵Ŀ��y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Ĉ�(ji��n)��(qi��ng)�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?���Ҳ�Փ���҂��]���x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ʷ�F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̵��ˡ���(du��)ʷ�F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��ɵ��£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Ȼ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R�Ĺ�(ji��)��;���nj�(du��)��ʒ�t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ʼ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}�ٵĸ�e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δ��ɵ���Ʒ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һ�q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Ȼ��ֹ��“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!”���ڲ����У�ʒ�tһ·�h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K�c(di��n)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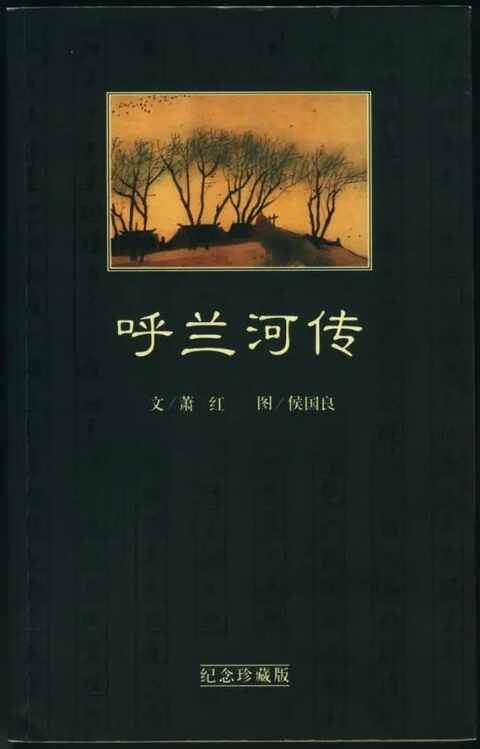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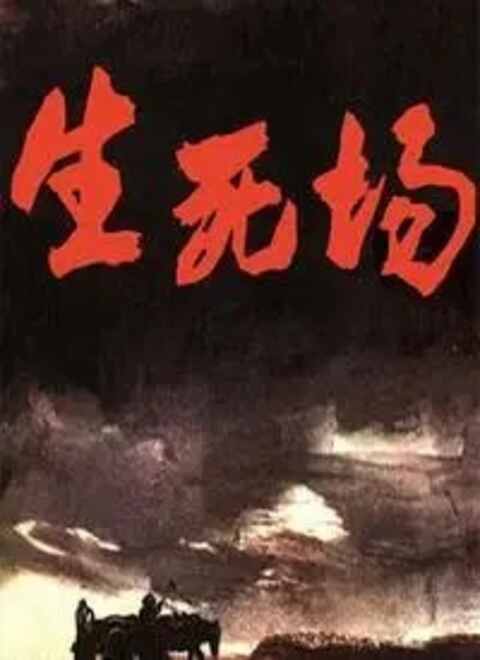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K�c(di��n)��ʒ�t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Ͳ��ң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Ů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Լ��ǿ��ú��صġ����nj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㯵ģ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̵���e���f�^��“Ҳ�Sÿ��(g��)�˶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l����֪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Y(ji��)β��߀�Ǜ]�п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ڰl(f��)���@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ԵĽ�¶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ڵӵı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ڷ⽨�����У��oһ���@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ۣ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Եı�������Į?
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Ґ�ʒ�t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ɐ۵�Ů���кܶ࣬���ɲ��b����ë����߹°��ď����ᣬ�挍(sh��)ͨ�ė�{����……Ψ��(d��)һ�����A�sһ��Ư����ʒ�t�Ґ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۵�ͯ�꣬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ĸ��飬��֮���쑑�˵��Ը�ʒ�t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ǿ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Ҳ��ȫ�w؟(z��)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ͬ�ڏ�����ĸҐ۸Һޡ���Ó���b��ʒ�t�ڸ����еı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Ұ��䲻�ҡ�ŭ�䲻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@�c(di��n)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Ʒ�ϵĴ�⡢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ԡ�
����“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(hu��)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Ů�˶����ױ��м����ͻ��룬����Ҳ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@����Щ���ۺ�ܛ���ľ��ʰ�”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t���˰ɡ�
����1942�꣬ʒ�t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;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g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2020�ꡣ�^�vʷ�ğ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h�졢̓�ã��ǂ�(g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˂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xȥ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ծ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ľ����ۺm��Ҳ�ڕr(sh��)�g�����в�ҊۙӰ��ֻ�ܸЇ@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͕r(sh��)�g�ğo�顣“��ز��ʣ��f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”��ǧ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أ��҂��sһֱ�ڴ��з���(f��)�m�p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f��,��Ϧꖼt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ՄЦ�g����Ҳ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ʒ�t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h�u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˼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