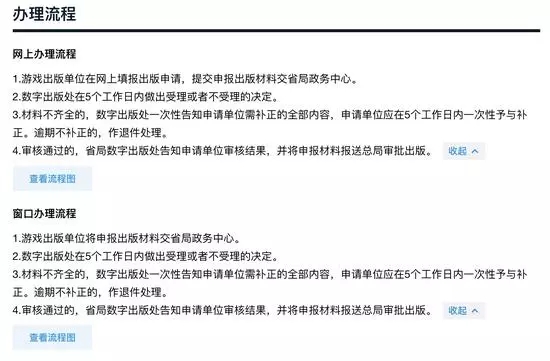“全國幫忙,武漢能夠過關!”鏡頭里的鐘南山,眼眶含淚,話語深沉。

如果不是背景提示,不是你了解他的信息,你或許很難想到:這竟是一位84歲的老人了。
已經說不清楚,這是鐘南山第幾次走上前臺。
時光荏苒。
整整17年前的正月初三,鐘南山臨危受命,出任廣東非典醫療救護專家組組長。
這是一種全新的病癥,當時連致病原因都搞不清楚。它來勢洶洶,許多沖在一線的醫生,都倒在未知病魔面前。
鐘南山卻對廣東省衛生廳提出這樣一個要求:“把重病人都送到我這里來!”
“我不是不怕死,只是仗著自己身體好。”鐘南山說。
那一年,他67歲。
還是這年的4月12日,疫情蔓延,民意沸騰,謠言如驚濤拍岸。新聞發布會前,鐘南山被授意“不要講太多。”
當他發言結束,有記者大聲追問:是不是疫情已經得到控制?
鐘南山再也忍不住了,大聲炮轟:
現在病原不知道,怎么預防不清楚,怎么治療也還沒有很好的辦法,病情還在傳染,怎么能說是控制了?
我們頂多叫遏制,不叫控制!
連醫護人員的防護都還沒有到位!
舉國嘩然。發布會第二天,衛生部換帥。月底,履新海南省委書記才5個月的王岐山,“火線”就任北京代市長。
又一個春節。
當有專家言談“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證據”,還是84歲老人第一時間,確定“新型冠狀病毒能夠人傳人”,并首度透露有一名病人感染14名醫生!自此,之前云蒸霧繞的一線迷情,被迅速廓清。一條條密集的快訊,開始分秒必爭,向全國擴散。
此時此刻,大江南北,長城內外,億萬中國人捧著手機,守候家中。他們心焦慮著,似乎沒有任何人,能比這位老人更能帶來安慰。
無他,只因他的名字叫鐘南山。
他的名字,等同真話。
沒有什么,比真話更能照亮這長空。

1月18日,84歲高齡的鐘南山奔赴武漢
鐘南山,一個大氣而恬然的名字。鐘南山多牛呢?下面就來詳細敘述鐘南山事跡,帶你解密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傳統文化中,南代表著向上的能量。山的南面,是為陽。
1936年10月20日,35歲的鐘世藩迎來第一個孩子。鐘家兩代單傳,此子的到來,被視為分外珍貴。而正處戰亂之年,孩子的到來,也帶給這個家庭無限勇氣。
為他起一個什么樣的名字呢?
湊巧的是:孩子出生的南京中央醫院,恰好坐落于南京鐘山的南面。
就叫鐘南山怎么樣?鐘世藩靈感所至,與妻子商議,二人一拍即合。
陶淵明詩云“悠然見南山”,但這位南山的成長,卻一波三折,步步驚心。
鐘南山出生第四個月,日本就轟炸了南京。鐘家毀于一旦,襁褓中的鐘南山,幸得母親和外婆拼命搶救,才從廢墟中逃過一劫。
1937年7月7日,鐘南山還未滿周歲,父親又帶一家老小,隨國民政府西遷的20余萬大軍離開南京,前往貴陽。沿途顛簸,風餐露宿不在話下,事后看,在南京城破前夕離開,又算逃過一劫。
但抗戰時期的貴陽,仍時時被戰火和硝煙籠罩。
1943年一個星期天,父母帶著鐘南山和他的妹妹到公園游玩。這時傳來尖銳刺耳的空襲警報聲。幾人來不及跑到防空洞,就在父母帶領下躲進附近玉米地。很快,遠處近處傳來一陣密集的轟炸聲。待到一家人安然趕回家,卻見自家房子化為一片斷垣殘壁。此時的感慨,唯有劫后余生的慶幸。
貴陽生活很辛苦。民間有順口溜:天無三日晴,地無三尺平,人無三分銀。鐘家全家老小,一頓飯能有塊醬豆腐下飯,已算美餐。
這困頓,一直到抗戰結束才稍有好轉。1947年,鐘世藩舉家再遷廣州時,鐘南山已經11歲。
這是個嚴父慈母的傳統家庭。
也是后來廣東醫學界的名門。
鐘南山的母親廖月琴,是廈門鼓浪嶼名門廖家之后。在那個年代,可算勇于打破時代藩籬的新女性。她求學協和醫學院高級護理專業,畢業后由當時衛生署派至美國波士頓學習高級護理。新中國成立后,擔任過中山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,是廣東省腫瘤醫院創始人。
父親鐘世藩,同樣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,后赴美國取得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。后創辦中山醫學院兒科病毒實驗室,成為全國最早創辦的臨床病毒實驗室之一。

鐘南山(后排右一)妻子李少芬(后排右二),父親鐘世藩(前排右一)母親廖月琴(前排右二)
都說虎父無犬子,但在這對學霸父母養育下,年少的鐘南山,卻極盡頑劣之能事。
他是家中長子,行事霸道,比如吃飯時雞蛋他要最大的,吃肉他也要夾最大塊。
他崇尚武俠之浪漫,12歲那年,趁家中無人,竟找一把大傘,模仿影片中的大俠,從三樓上跳下去。原本幻想像游俠一樣空中飄蕩,卻不想傘邊向上翻卷,而他本人重重墜落地上。萬幸,下面是草地,腿和身體沒有大礙,鐘南山癱在地上足足有一個小時,才緩解劇痛站起來。
他學習稀爛,小學就留級。從貴陽到廣州升了四年級,卻整天貪玩,升級考試未能過關。
多年后,再回顧鐘南山這段“無法無天”的歲月,卻不難發現,“頑劣”性格另一面,或許正潛藏著獨當一面、敢言敢行的底色。
與此同時,父母的人格投影,正以潤物無聲的方式,澆灌這位少年的心性。
2008年5月,已經72歲的鐘南山在一次演講中,這樣回顧母親,“我到現在還記得媽媽是怎么對待其他有苦難的人。”
那時年幼,周邊鄰居常有人家貧穿不起衣服,母親便常拿出衣服,接濟鄉鄰。
1955年,鐘南山考上北京醫學院,而他在華師附中的一位同學考上了北大物理系,卻家境緊張,窘迫下向鐘南山開口:“能不能借我點錢,我坐火車沒有錢。”
鐘南山回家將此事告訴母親。母親很為難:“南山,你不知道,我們為了準備你的錢已經很困難了……”
卻不想,就在鐘南山出發前幾天,母親再度將他叫到面前,手里拿了20元錢,對他說:“把這些錢拿給你同學吧。”這幾乎是當時三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。
如果說母親教會了他善良,父親則指引了他的人生。
父親是有名的兒科專家。從年少起,鐘南山便耳濡目染父親專注救人的醫德才學。晚上,也常有家長帶孩子去他家問醫。幾天后孩子康復,家長非常高興,不茍言笑的父親也露出開心的笑容。
這笑容感染了鐘南山,他那時就有強烈感受:做醫生能幫助別人,得到社會尊重,這是一份有價值的事業。最終跟隨父母走上這條并不平坦的道路。
對于想要繼承醫者衣缽的鐘南山,父親也是寄望頗深。
1971年,鐘南山于北京醫學院畢業并留校任教11年后,回到廣州,任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內科住院醫師。
一天,一向不愛說話的父親突然問了他一句,“南山,你今年幾歲了?”
鐘南山沒明白父親用意,恭恭敬敬回答:35歲。
父親深深嘆了口氣:唉,都35歲了,好可怕……
父親再未多說,鐘南山卻徹夜難眠,他明白父親的苦心,是擔憂他碌碌無為一事無成。相比同年齡段的優秀醫生,他的差距太大了。
這句話,鐘南山記了一輩子。也是從這一年起,他奮起而為,他的醫學事業由此啟幕。

1979年,鐘南山迎來命運的轉折。
那時的他,已經43歲了。
這一年,他通過國家外派學者資格考試,爭取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向英國派遣的第一批留學生,趕赴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及倫敦大學呼吸系進修。
這一代人,被運動耽擱了很多時間,這正是他充電補強的機會。
到異鄉他國,遭遇的首要難題就是語言關。此前英語考試,鐘南山只拿到52.5分。
怎么辦?先練聽力。頭幾個月,每天做完實驗后,晚上都要再加一個小時,練習聽力。反復聽磁帶,邊聽邊寫。為此,他竟記了好幾打筆記本。
在接受央視采訪時,鐘南山還透露一件隱情。為練習英文,他就用英文給國內的父親寫信。每次父親回信總將信封塞得鼓鼓。原來,父親在英文回信之外,還把鐘南山的去信一并寄來了,并用紅筆對每句話字斟句酌地修正。哪里表達不當,哪里表達不清楚,批改得一清二楚。
就這樣持續一年多,鐘南山的聽寫能力迅速提升,可以和英國人基本無障礙交流了。
而接踵而來的問題,再度令鐘南山壓力山大。
依照當時英國法律,中國醫生資格是不被承認的,無法單獨為病人治病,只能以觀察者身份參與查房和實驗。
而在鐘南山導師弗蘭里教授看來,不實際操作很難學到內容,于是他致信鐘南山——不需要在英國待兩年,待八個月就可以了。
鐘南山很焦慮,甚至后來面對非典等疫情,也未曾帶給他這樣的不安。他擔心就這樣無所成績回去,無顏見江東父老。
1980年1月6日,鐘南山與導師弗蘭里第一次會面。教授說,“你先看看實驗室,查看病房,一個月后再考慮做些什么。”會見只有短短10分鐘,對方的淡漠卻激發了鐘南山的好勝心。他打算拼一把,向弗蘭里證明自己的能力。
有天,他和英國醫生查房時,發現一位患肺原性心臟病的亞呼吸衰竭頑固性水腫病人,引發醫生關注。這位病人已使用一周利尿劑,水腫卻未見消退,命懸一線。
醫生主張繼續增加一般性利尿劑量,鐘南山卻另辟蹊徑,運用中醫辯證法,斷定病人為代謝性堿中毒。他主張改用堿性利尿劑治療,以促進酸堿平衡,達到逐步消腫效果。
改用鐘南山治療方案后,患者中毒癥狀完全消失,通氣功能改善。這一次“小試牛刀”,令英國人對鐘南山刮目相看。
為驗證導師一項名為“一氧化碳對人體的影響”的研究,鐘南山更直接以自己為實驗體,吸入一氧化碳,抽血化驗。實驗持續兩三個星期,他吸入的一氧化碳之多,相當于一小時抽60多根煙。
最終,該實驗在證實弗蘭里教授演算公式的同時,也發現其推導的不完整性。
弗蘭里看了結果非常高興,論文最終在英國醫學委員會發表。之后,弗蘭里問鐘南山打算干多久,鐘南山反揶揄他說“您不是說只給我八個月時間嗎?”弗蘭里立即糾正,“不,你愛干到什么時候都可以。”
英國留學兩年間,鐘南山通過與英國同行合作,先后取得6項科研成果,完成7篇學術論文,其中4項分別在英國醫學研究學會、麻醉學會及糖尿病學會上發表。
1981年,當他婉拒了英國愛丁堡大學極力挽留他在皇家醫院工作的機會,決意回國,導師弗蘭里特意給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寫去一封熱情摯誠的信:
“在我的學術生涯中,曾與許多國家的學者合作過,但我坦率地說,從未遇到過一個學者,像鐘醫生這樣勤奮,合作得這樣好,這樣卓有成效。”
那天晚上,鐘南山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句話:
“我終于讓他們明白了中國人還是有值得別人學習的地方。我第一次感覺到做中國人的驕傲。”
也是從那時起,他更堅定了自己的人生信條:相信實踐,敢于質疑,不迷信任何權威。
歸國后,鐘南山因在呼吸科方面的研究和專業水準,很快聲名鵲起。
但讓他“紅”到圈外的,卻是非典時期的敢言能為,力杠權威。
那是2002年12月22日,醫院接診了一個來自廣東河源的肺炎病人,病情很奇怪,持續高熱,且用各種抗生素都不能緩解癥狀,只好加急轉診過來。“才短短幾天,肺就全白了,肯定不是一般細菌感染。”
2天后,河源傳來消息,之前接觸過該病人的7名醫務人員和一名家屬都發病了,癥狀和病人一模一樣。
鐘南山考慮會不會是急性肺損傷,就試用皮質激素進行靜脈點滴注射。
他判斷病情已是中末期,勝算不大。但意外的是,到了第二三天,病人情況明顯好轉。在先后治療六七個病例后,鐘南山摸索出一套治療和康復的辦法,后總結出“三早三合理”的經驗。
然而,到了1月18日,一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驗來到他面前。
國家疾控中心從北京發來報告稱:從廣東送去的兩例“非典”死亡病例肺組織標本切片里,在顯微鏡下看到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體顆粒圖像。當天,新華社向全國發布消息:近期一直困擾廣東人民的“非典肺炎”病原體基本確定為衣原體。
這一信息也被央視在新聞聯播中報道。全國各類傳媒紛紛轉載。人們也得到極大振奮,從人性來說,人們都愿意相信積極的消息。
壓力是巨大的。
衣原體并非新發現的致病源,也有較好治療方法,這意味著離戰勝它為時不遠。
但是,臨床經驗告訴鐘南山:如果是衣原體感染,患者應伴有上呼吸道炎癥,且抗生素應該有效。然而,鐘南山所接觸過的“非典”病人,均無這些特征。如果按照應對衣原體的方式去治療,采用皮質激素反倒會助長傳染,會被嚴格杜絕。若如此,大量命懸一線的生命,還有沒有希望挽救?
怎么辦?當時,鐘南山是廣東“非典”醫療救護專家指導小組組長。他的態度至關重要。就在整個廣東都望向他的時候,這天下午,鐘南山明確表達態度:
衣原體可能是送檢兩名死亡病人的致死原因之一,但非病因,臨床癥狀不支持衣原體感染的結論!
這幾乎是以一人之力,抗拒全國輿論。
有朋友悄悄問他:“你就不怕判斷失誤嗎?有一點點不妥,都會影響院士的聲譽。”
鐘南山回答:“科學只能實事求是,不能明哲保身,否則受害的將是患者。”他記得父親給他的告誡,任何時候,都要誠實、鮮明地亮出自己觀點。
2月26日,國家疾控中心再次報告檢出衣原體,并肯定衣原體是“非典”致病原,并有人帶話給廣東方面,要求他們統一口徑。
但一眾醫生在鐘南山激勵下,堅守住了實事求是的底線。他們依舊采取自己療法,應對未知病魔。更有醫生激動表達,“如果SARS病原體是衣原體,寧愿把腦袋割下來!”
與此同時,鐘南山牽頭,與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合作,開始攻關非典病原。
3月25日,美國國家疾控中心和聯合攻關的相關大學微生物系宣布:“非典”病原體是一種冠狀病毒。
4月11日,鐘南山牽頭的課題小組也收獲成果,也從40余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雙份血清檢測中,分離出兩株冠狀病毒。
事實證明,他們的堅持,是對的。
但在這種情況下,鐘南山還面臨一個困局:因北京專家對病原體判斷有誤,先前重視不足,病毒已擴散,全國人心惶惶。另一方面,仍有官員宣稱“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”。
要不要說真話?
鐘南山左右為難,去北京參加全國新聞發布會前,他特意到父親墳前默立了許久。
答案我們都知道了。他打算不悖良知,“當時全國疫情都在蔓延,我在的呼研所醫生都倒了20個了,實在不能扯淡。”
真話,和真藥一樣重要!
正在這次發布會上,他說出了本文開頭所提的驚人之語。疫情,根本沒有得到控制!
由此,全國應對非典的局勢,陡然加壓。
當人們敢于直面問題,才能向著解決問題,邁出堅實的步伐。
而鐘南山當時所在的呼研所,也開始顯現治療成效:因其收治皆為重癥病人,到4月中旬,101名重癥病人,已有87人康復出院,搶救成功率達到87%。
整個非典期間,他們院創造了全國最高的危重病人搶救成功率,超過香港。這一經驗迅速普及,及至非典后期,因應對有效,人們對非典的恐懼已煙消云散。
5月16日,美國西雅圖由全美胸肺科學會舉辦的2003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,鐘南山關于《中國“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”(SARS)的發病情況及治療》專題學術報告,贏得全世界各地1200多名專家學者的掌聲。
第二天,美國電視專欄《今日美國》對此詳細報道,認為“中國大陸SARS的發病率已明顯下降,令人鼓舞。”
大會主席比思爾教授在總結中更強調,“我們獲得了防治SARS經驗的最新報告,亞洲經驗將為全球應對SARS的有效控制提供有價值的啟示。”
這一年,鐘南山成了應對非典的中國英雄。
他被廣東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的特等功,又被授予國內衛生系統的最高榮譽稱號——白求恩獎章,還被評為了“感動中國2003年度”十大人物之一。

光環總是明亮的、暫時的,對于鐘南山來說,更為真實的生活,是曠日持久的辛勞。
為應對非典,時年67歲的鐘南山曾連續36個小時不眠不休不下火線,為此,累得自己也感染普通肺炎。怕引起外界誤會,他將自己隔離家中,自己給自己掛吊瓶診治,5天痊愈后,又匆匆趕回診室。
同樣少有人關注的是:非典之后,當全中國都松一口氣,這位老人又返身踏上新的征程。
他早過了退休年齡,卻很多年沒休息過了。
“我有周六和周日,但我要干活。”
近年來,他把專業方向放在慢性阻塞性肺炎的防治工作。該病在中國超過1億人患病,是中國人第三大主要死因。而這,也是他在英國留學時的研究方向。
如今,他的研究小組,已經首次從流行病學證實,生物燃料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,并首次發現兩種含硫氫基的老藥,可用于預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發作。
關于此病,世衛組織的治療指南只針對有癥狀的人。但是,當患者有癥狀再去看病,肺功能往往損壞一半以上了,已經失去最佳治療時間。
2017年9月7日,鐘南山、冉丕鑫有關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論文發表在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》上,隨機、雙盲、安慰劑對照的實驗結果顯示:使用噻托溴銨的一組患者和使用安慰劑的一組患者相比,肺功能改善率明顯提升,從一般的50-60ML提高至120-170ML。成果引發全球呼吸疾病領域的轟動。
而鐘南山及其團隊相關成果,被寫進世衛組織編撰的新版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防治指南,兩篇論文分別被評為《柳葉刀》2008年度最佳論文、2014年度國際環境與流行研究領域最佳論文。
這被鐘南山視為非典之后,最為欣慰的成績。
相比于他的術業有專攻,同樣還有很多今天年輕人所不知的,是鐘南山當選全國政協委員、人大代表后的一次次公開發炮。
非典后,他曾深刻思考,“個別領導的問題,我想關鍵是選拔方式問題。為什么有的官員只是對上負責,因為上面對他將來的提拔、發展有好處,他工作出發點是對上面負責,而不是對下面負責,向群眾負責。我覺得還是要有上級領導和人民群眾的一致性。否則就像這次有的官員一樣,最后是要垮臺的,免職的。
2006年兩會,他質問藥監局領導:“一藥多名”、“換個名字就漲價”的批號是怎么拿到的?
在禁煙的問題上,他公開說:相關機構又管賣煙又管控煙,這怎么可能?這完全是對立的事情!
2008年6月,他批評珠三角空氣污染:“50歲以上的廣州人,肺都是黑的!”
2009年,他在兩會上批評部分代表“10分鐘發言,8分鐘用來對報告、對自己極盡吹捧吹噓之能事。”
2010年,他炮轟一些黨報刊登性病廣告:這些性藥、保健品以中藥名義出現,實則含有西藥成分,因劑量成倍添加,極易損害健康。為此他曾籌備六年尋找證據,親自買下保健品帶到藥監局檢測,形成議案上會諍言。
2011年,一個煙草公司的專家因降焦減害當選院士,他又批評:
降焦減害,還成為院士,這太荒謬了。降焦是做出來了,但重要的是,焦油降了,危害并沒有減少,所有的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。企業用降焦的噱頭作宣傳,賣得還更好了!
2013年,他大聲疾呼,健康遠比GDP重要,提出“霧霾比非典更可怕”,引發爭議。

他多次呼吁公布PM2.5數據,指出,“灰霾(霧霾未引發重視前的稱謂)與肺癌有莫大關系!”
當時方舟子與他論戰,認為他夸大危害。鐘南山則有理有據回應,“PM2.5直接侵入肺中,人體的生理結構決定了對PM2.5沒有任何過濾。”兩年后,世衛組織將霧霾列為一級致癌物,印證了鐘南山的觀點。
2014年兩會上,他“炮轟”五年醫改沒有明顯突破。“看病難、看病貴沒有明顯緩解。”
這也是多年最令他心焦的話題之一。
有記者問及暴力殺醫、傷醫,他曾這樣說:“我國的醫療體制被推向市場之后,好處是有了競爭,使醫療質量有了很大提升。但不好的是,醫療公益性減弱、政府投入減少,病人看病都要自掏腰包,這些因素把醫生和患者推向了對立面。”
他為過度醫療、醫生見利忘義現象心寒,但又無奈承認“現在我國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的收入80%以上藥靠醫院創收,這種市場化必然會對醫德形成挑戰,亂開藥、亂檢查也就不足為奇。”
他有個心愿,持續加大政府投入,“我最希望看到的是醫療公益性的加強,減少醫院對藥品加成和其他經濟利益的依賴,這樣醫生才能從自己做起,修復治病救人的正氣。”
2016年,鐘南山80歲。那年生日,他收到一份禮物。一幅字,四個字,“敢醫敢言”。
晚年的鐘南山,儼然超脫他早年的醫者形象。所謂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莫過于此。
或許,他在以另一種形式,踐行他少年的豪俠夢想吧。
可人們終究忘了:鐘南山也不過是一個人。
前不久,朋友圈狂刷鐘南山的健身圖。人們贊嘆,這位名滿天下的學者,是健身能手,原來也曾是名“運動員”。1959年,23歲的鐘南山,在首屆全運會上,他以54.4秒的成績刷新了男子400米欄全國紀錄,并奪得男子10項全能冠軍。媒體還熱贊:這是運動世家。前述全運會上,鐘南山還與妻子李少芬結緣。
李少芬,1952年,16歲的她就成為中國女籃首批隊員,1964年摘獲匈牙利、法國、羅馬尼亞、中國四國籃球邀請賽冠軍,現為中國籃協副主席。
他們的女兒鐘惟月也不簡單,曾獲短池游泳世錦賽100米蝶泳世界冠軍,1994年更曾在短池游泳錦標賽上打破世界紀錄。
但很多人并不知道,這些熱傳的健身照,很多也是前些年照片了。
“非典”及之后的繁忙工作,已令鐘南山身體大不如前。
2005年,他得了心機梗阻,做手術裝了支架;
2007年還出現了心房心房纖顫;
2008年,他得了甲狀腺炎,短短兩個月瘦了10斤;2009年又做了鼻竇手術。
如今,又十年過去,再強壯的肉體,也經不起時間與辛勞的磨礪。
明白這些背景,或許你才更難理解:他為何,還要拼命向前呢?
一切,就像一場輪回。
將時間倒回1976年,那是75歲、已經退休的鐘世藩伏案圖書館,正用一只放大鏡閱讀文獻。
他的眼力大不如前,只能經常蓋著一只眼睛,只用一只眼睛閱讀和寫作,而讓另一只眼得到休息。后來,因患白內障,視力很差,寫作時幾乎整個臉貼在桌面上。
他在全力書寫最后一部心血之作《兒科疾病鑒別診斷》。
那時,鐘南山很不理解父親:“你身體都這樣了,為什么還要寫書,就不要寫了吧?”
鐘世藩的回復簡單,甚至有些“粗暴”:“不寫書做什么,難道要我等死嗎?”
1987年,臨去世前一天,鐘世藩還在跟鐘南山講:用電磁場來切割病毒的液體,讓病毒產生一些變化,看看這樣會不會對病毒有殺滅作用。
他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,無力回天。面對死亡,他鎮定吩咐兒子:“找人弄來電磁鐵,準備做下一步的實驗。”
2019年,鐘南山面對央視采訪時,首度吐露了他對這位不善言辭、既敬又怕的父親的心聲:
爸爸你曾經說過,一個人來到世上,留下一點東西,這輩子就不算白活了。
現在我已經80多歲了,我慢慢懂得了,你的愿望我已初步實現。但是我還是不會滿足,我有兩項工作還沒完成,要是這兩項工作我達到了以后,那我是真正地達到你的要求。
畢其一生,有位父親以他近乎枯燥而又偉大的言行,塑造了兒子的高度。
鐘南山沒有透露兩項工作是什么,但他晚年曾多次談起最后的奮斗:
“第一就是促進呼吸中心全方位建成;第二,我已經研究了26年的抗癌藥,我希望把它搞成,現在已經走過大半路程;第三,我希望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早診早治,形成一個全國的乃至全世界的一個治療思想。”
如今,三個追求尚未實現,當武漢告急,當全國警報,當前線專家也因感染新型肺炎而倒下,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,又一次義無反顧,扛起歷史的重擔。
接到通知后,1月18日傍晚,買不到機票,便像普通乘客擠上傍晚5點的高鐵列車,火速趕往武漢。一路上只靠著后背,合眼略作歇息。
他再度使出全力與病毒賽跑:在武漢奔赴多個醫院了解疫情后,19日又趕往北京,參加國家衛健委會議;20日只休息4個鐘頭,便從早上6點開始工作.....25日再匆匆趕回廣州,奔赴一線救治新型肺炎重病患者。
基辛格在《論中國》中說過: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,保護的很好。
而這種勇敢,從不是一個人,而是持續地燃燒在他們之中堪稱脊梁的那批人身上。
他們如風中之火彌足珍貴,亟需一個民族以推崇良知與公義的熱掌,小心呵護。
“人不只生活在現實中,也生活在理想中。”鐘南山說。這是他中學老師的贈語。
他已為子女和孫子孫女留下寄語:你們要記住,鐘家的優良傳統,第一個,就是要永遠有執著的追求,第二,辦事要嚴謹實在。
他已將對父親的致敬,有力傳遞給下一代。
祈愿先生再度凱旋。
亦愿未來中國,更有千千萬鐘南山。

鐘南山辦公桌后面的窗臺上,擺著一個長方形匾額,上書“勇敢戰士”四個字,那是廣州市護士學校學生送給他的。而條幅右邊寫著鐘南山說過的一句話:“醫院是戰場,作為戰士,我們不沖上去誰沖上去。”